
▲
科研团队合影
12月13日,《自然》(Nature)选出2019年度十大杰出论文(10 remarkable papers from 2019),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鲁伯埙与丁澦课题组(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脑科学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光科学与工程系费义艳课题组(微纳光子结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超精密光学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研究成果《HTT-LC3连接化合物对变异HTT蛋白的等位基因选择性降低》(“Allele-selective Lowering of Mutant HTT Protein by HTT-LC3 Linker Compounds”)入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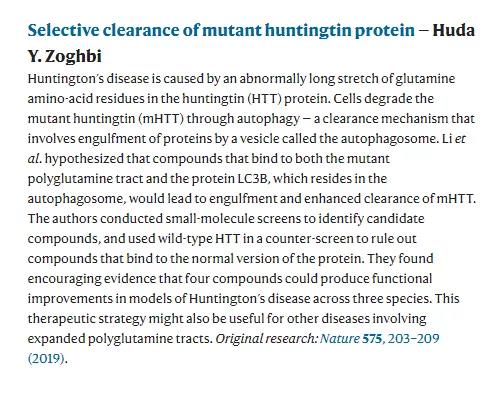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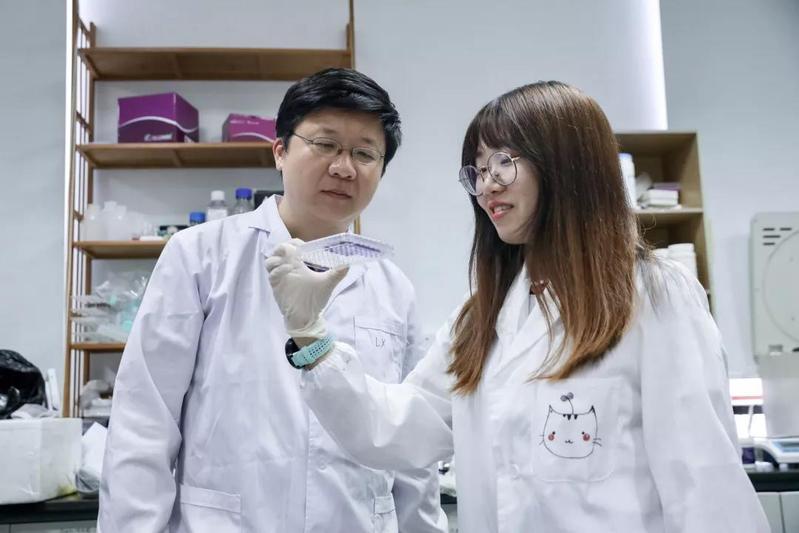
▲
鲁伯埙教授(左)和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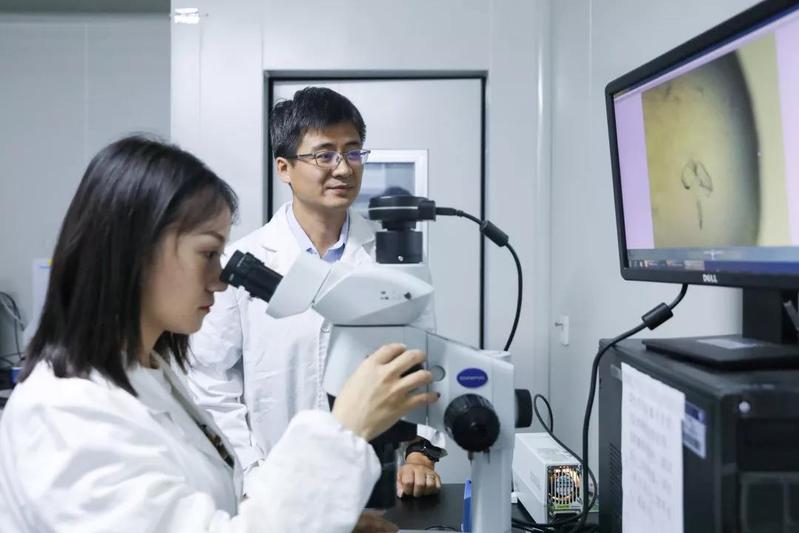
▲
丁澦副教授(右)和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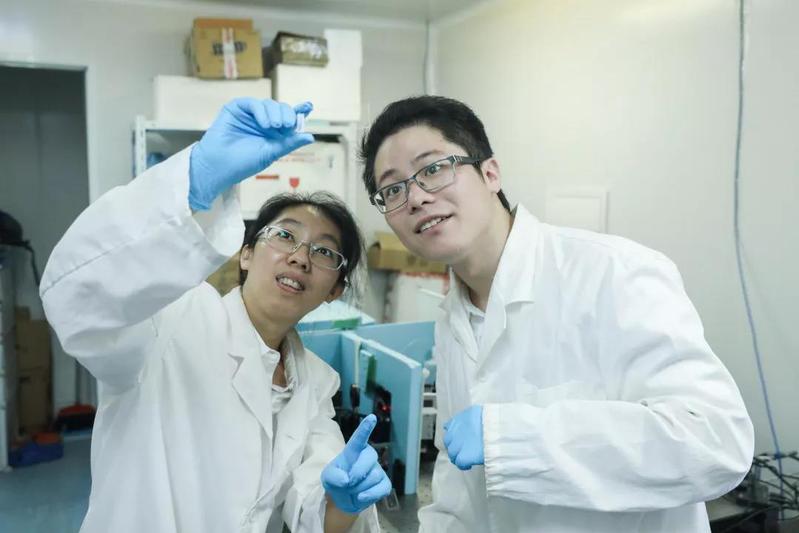
▲
费义艳副研究员(左)和学生
2019年复旦大学多篇学术文章刊登Nature,Cell等杂志,科研硕果丰硕傲人。这些硕果的背后是因为有像鲁伯埙、丁澦、费义艳等这样一批复旦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初心坚守在科研岗位上,他们用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实验数据和跨学科的团队合作诠释着“团结 服务 牺牲”的复旦精神,为复旦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上交着一份份优秀的答卷。
提起鲁伯埙,2017年在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建院90周年之际,《复旦人》杂志对他做过独家专访,正如他自己所言“从未想过科研以外的人生”,而他也用实际行动深耕着他的科研人生。

鲁伯埙:从没想过科研以外的人生
本文来源《复旦人》第27/28期(合刊)
1999年,鲁伯埙考入复旦读本科,先在理科基地班(下面简称“理基班”)读了两年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基础课后再选专业,这期间他唯一选过的生物专业课只有一门“普通生物学”。大一大二所有的课中,凡是带物理的课鲁伯埙基本上都是满分,但到了理基班选专业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自己最擅长的物理学,而是选择了生命科学。据鲁伯埙回忆,复旦的生命科学学院全国最顶尖,所以非常难进,“记得理基班有一个分专业考试,选生物的是考得最高的,绩点也是最高的。”
鲁伯埙承认自己那时选择生科确实是受了“生科热”的影响,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要在科研上有一番建树:“物理学已经发展很成熟了,你没有150的智商想在科研上有突破是很难的,但是生命科学就不一样了,它待解决的问题最多,所以也最容易做出成果来。”
如愿进了生科后,由于前两年缺乏生物方面的训练,比起大一立志就学生物的同学,鲁伯埙并不是很能适应生科的学习方式。一向以逻辑见长的他实在不喜欢那些需要背的课,在实验课上理基班同学的动手能力也相对较弱。在生理实验课上还发生过一件让鲁伯埙至今仍“耿耿于怀”的事:实验的内容是给兔子做动脉手术,在这之前需要先给兔子注射麻药,他们理基班同学那组却连续打死了两只兔子,最后只得被拆散到别的组。
“我觉得我们称得很准,量得也很准,但是一打很快兔子就死了,我们给它做人工呼吸也活不过来。我们当时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怀疑是书上的麻药剂量公式写错了,但因为其他组的兔子也没有死,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所有生物专业课里,给鲁伯埙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黄伟达老师的“生物化学课”。因为刚读大一时他就准备选生物,所以曾经偷偷跑去旁听黄伟达老师的生物化学课,那时候他总是拜托生物系的同学在生物楼的107教室帮他抢座。此外,他对梅岩艾老师的生理课也很感兴趣,因此后来就进了梅老师的实验室,大三大四这两年常常在135房间做实验。
实验室里有一个 “夜猫子型”的研究生师兄,为了能在晚上十一点之后继续做实验,他们还需要时不时“跳个楼”。“当时每天晚上十一点就会锁门,我们有时候做实验做到很晚,回不去,然后我们就会从二楼的窗口直接跳到一楼进门的一个水泥台。”说起求学时代在生物楼里发生的趣事,一直严肃的鲁伯埙也忍不住笑了。
2003年他本科毕业,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了生物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据他回忆,当时生科院140多个本科生中有近四分之一都出国深造了。博士的前五年,鲁伯埙从没想过科研以外的其他工作,直到2009年博士快毕业时遇上次贷危机,经济萧条导致美国的很多实验室都无法正常维持,像生物这样“烧钱”的学科想申请到足够的经费做科研就更是难上加难,那时科研的工作岗位,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都逐渐饱和。于是,他选择毕业后去“诺华制药”工作,希望通过接触产业界了解“生物医学研究”与“实际制药”之间的距离,为科研争取更多的资源。

在“诺华制药”工作期间,鲁伯埙回国开会,顺道回母校拜访几位老师。本科期间的实验室导师梅岩艾邀请他在生物楼107教室做一个学术报告,生科院的马红院长参加了报告会,并向他介绍了“青年1000人计划”,鼓励他申请。当时这个项目的申请还有五天就要截止了,鲁伯埙一边开会,一边整理申请材料。申请过程很顺利,他就这样成为了同届理基班生科方向同学中的第一个PI(Principle Investigator)。
十年后再回到求学时代的生物楼,鲁伯埙的第一感觉是“没怎么变”:生物物理系的很多老师都是熟悉的,梅老师的办公室还是在原来的位置,107教室的椅子也还是有很多翻板翻不起来……唯一改变的就是他的角色,他在138房间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实验条件有限,没有足够的空间,既要运作自己的实验室,又要和学校的很多行政部门打交道,千头万绪,无从下手,“多亏有本科时候就认识的这些人的帮助, 实验室才很快地一步步建好,生科一直给我一种家庭的温馨感。”

论文背后的故事
文/鲁伯埙
1. 早在2012年就有这个想法,但是用我当时已知的技术做光筛选要投入几百万经费和很多人力,不知道能不能筛出来,不太敢做。后面青年教师俱乐部晚餐的时候了解了光科系费义艳老师的工作,有很好的方法,才得以实行。后来蛋白质生化方面有很多地方没有经验,机缘巧合下学院安排丁滪老师帮助我的工作,一下就推进起来了。
2. 开始筛选出两个化合物后检测效果并不好,重复过很多次准备放弃了。有次食堂聊天时受启发突然想到,我们一直按之前的经验主要较高浓度(10μM),而按照我们预测的“胶水”,可能在较高浓度下不起作用,因为胶水分子会分别跟两种蛋白结合,而不会把它们拉倒一起去。只有最合适的浓度,才会起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回去检测nM级别的各个浓度,就看到了效果。
3. 在寻找化合物与变异HTT蛋白结合位点时,我根据已有的基于领域已有权威文献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很有可能的假说,即化合物识别了N17和Proline-rich domain的interface。按着这个假说,我设计了一套基于FRET的检测方法,让一个博士生和一个本科生做了很久,但是结果跟原本的假说越做越不符合。而那期间,我们的另一个项目则取得进展,提示了我另一种可能,即化合物识别的扩增polyQ的新浮现的特殊构象。一试之下果然如此,而且一下把药物的用途拓展到了别的polyQ疾病。
4. 文章数据基本在2018年9月就完成了,我给Nature和Cell投了Presubmission,很快都回信说感兴趣,邀请我投全文。其中Nature的编辑回信很长很认真,感觉是不是兴趣更大,所以后面投了Nature。中间还有个插曲,收到Presubmission回复当天还挺高兴的,结果反而不小心摔骨折了,而且骨折的是右臂,所以右手几个月不能动,工作和生活都靠左手,一直到2018年底才开始忍痛双手开工写文章,最后2月初投稿。
5. 投稿后一审意见很不错,不过还是有蛮多要补的实验。我们安排了五个参与实验室同时开始全力补实验,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
6. 稿件接收后得知Huda Zoghbi院士会写News and Views评论,写信给她表示感谢,她回答说“It is really a beautiful study and I hope it can translate nicely. ”,并且给了很好的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组稿|复旦大学校友会
来源|《复旦人》27/28期(合刊)
复旦大学官网、BioArt公众号
编辑|邓丹
服务校友 服务母校 服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