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的一天,一列湖南湘潭开出的绿皮火车缓缓驶入上海站,易行健和朋友拎着行李下了车,第一次来到上海。在那个没有地图的时代,他和朋友迷了路,绕着上海站转了一圈,花了40分钟才找到公交站,坐上开往城市东北角的车,那一年他26岁。
20年后,电话另一端的他仍清晰记得初见复旦的时刻:“校园里面很安静,各类讲座非常多。当时北区(现在本部)的高楼也不多,草地也很舒服,学术与学术氛围很浓厚。而南区就很生活化,有卖麻辣烫还有烧饼的。”他当下决定把复旦定为自己考博的第一志愿,随后如愿被录取,师从谢识予教授。
“复旦读博的三年是很快乐的,是我非常怀念的一段生活。”易行健说道。在采访中,他多次提到复旦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精神:“自由而无用”,在他读博期间,复旦为他提供了多样化的学术选择,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和比较广泛的学术视野和经济学问题意识;此外,这样的价值观也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宏观、长远的视角,也赋予了他一种超脱现实束缚的精神世界与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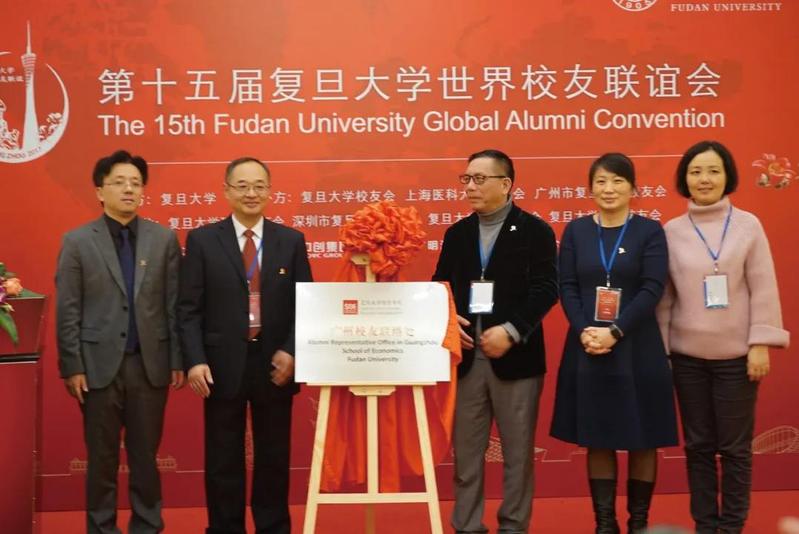
易行健教授(左一)参加第十五届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
从湖南湘乡的农村,到两年的车间工作,再到湘潭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从博士毕业后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到在中国社科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再到后来的远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访学;2014年9月,易行健顺利成为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的首任院长。
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己姓名背后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桃李路,自此始
1974年,易行健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户农村家庭,是家里的老大和长孙。当时的中国刚刚经过“文革”,经济凋敝,百废待兴。“那是一个很短缺的时代,我小时候一星期能有一顿肉吃,那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易行健回忆道。在当时,他很多时候和自己的爷爷待在一起。
易行健的爷爷也是一名教师。在解放前,他上了高中,并在乡里做中学老师,但在随后的政治运动当中被打成右派,直到1978年“平反”后才恢复了教师的身份。当时,易行健跟爷爷住在学校里面,前后断断续续生活了大约7年时间。在此期间,易行健陪着爷爷与老师们聊天,听他们讲新闻、说报纸,讨论国家大事以及学生的情况,还时常谈起中国的文化、历史、古诗词等等。他还和爷爷一起去做家访,一天晚上走访几家学生,“当时的农村比较尊师重教,有些家庭自酿米酒,爷爷也就喝上两杯”,易行健回忆道。在他看来,这段时间不仅是学习启蒙,而且让他接触到了教师这个职业。
这种教书育人的情怀,为易行健之后选择教师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从机床车间到经济学课堂
1992年,抱着对机械专业的兴趣,易行健进入湖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修学机械制造与设计,并在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湘潭市纺织工业局下面的纺织机械厂工作。“我是正儿八经在第一线开过近两年车床,在学校期间学校多次组织金属工艺实习,湘潭钢铁公司、湘潭柴油机厂、襄樊轴承厂、湖北十堰的二汽集团以及云南高原汽车厂等很多工厂都去过”,易行健回忆道。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很快发现,机械制造行业和他的职业期望偏离较大,促使他逐步思考现实经济问题,多种因素驱使他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考经济学的研究生。
“我是1995年6月毕业的,然后下半年就决定去考研究生了”,易行健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重拾改革开放的信心,此时正值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识逐步达成的阶段。在易行健面前,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复旦宋承先教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易行健打开了经济学的大门。初学经济学,易行健也摸着石头过河,其间还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尹伯成教授的配套习题集来做。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阅读过程中逐渐找到了经济学科和他自己知识的连接点:物理和数学,这两个学科的诸多逻辑与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经常被用到,而且现实中的社会经济运行也在为易行健提供活生生的案例。随着阅读的深入,易行健还发现了尹老师习题集里的一个问题似乎不太清楚,他写了封信寄到复旦大学,而尹老师也在认真阅读后,仔细地撰写了回信,这让当时的易行健更有了学习的自信。
每一个成功考研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付出。因为白天需要在工厂上班,所以易行健只能在晚上备考,从晚上7点学到半夜,确保每晚有5个小时的学习。此外,易行健还利用自己所学的机械制图工具,将宋老师书里所有的经济学图形一起画在了一张零号图纸(1189mm x 841mm)上,挂在墙上每天观摩,“考之前我就说,其他的能不能考好我不知道,但是经济学我一定能考好,因为西方经济学上面的图我可以说非常熟悉了。”易行健笑着说。但是这种学习也并非死记硬背,采访期间,易行健还特意用他喜爱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武学来做解释,不是要记住具体的图形,而是要理解一招一式后面的思维逻辑,“存其意忘其形”,这才是最重要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易行健顺利考入湘潭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本,易行健计划毕业后进证券公司,但是后来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学习考试,他发现自己对抽象的思维逻辑,以及中国的宏观经济金融运行更感兴趣,于是又下了读博的决心,并在2001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数量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
“那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当然是非常高兴的”,易行健在电话另一端略带兴奋地说,“当时的录取通知书还不像现在这样漂亮,就是一张小白纸上写着报到的要求,比如时间地点,再盖着研究生院的章”。此时正值新千年初始,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0多个年头,中国万象更新,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已经矗立在浦东。常言道,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来自复旦的小白纸通知书,就如同从苦难当中振作过来的中国,虽然无华,但却在其中孕育着梦想和希望。
在复旦:那些自由而无用的日子
16年前,易行健是复旦北苑的第一批入住者。复旦的生活是充实的、也是惬意的。博士期间的课程并不算太多,易行健更多的时间主要用于阅读经济学典籍与文献。“复旦当时的书店非常多”,易行健是复旦周边书店的常客,常买些经济学读物,同时也广泛搜集英文典籍,这部分资料则需要交给打印店,“复旦有一个叫日月光华的BBS,我们可以在上面发打印任务,然后打印店就在上面抢单子。”当时的易行健不会想到,到毕业时,他的书和资料装了二十个箱子,“大的箱子有三四个啤酒箱加起来大,小的差不多是两个啤酒箱大小。”
除了做学术、读文献,易行健也有现在年轻人的爱好,看网络小说,但不是在门户网站,而主要是在日月光华BBS上面看。他看的是自己最爱的武侠小说,当时BBS有专门的武侠版块,同学们从网络各处搜集小说,转到上面,一同讨论剧情,“我把上面的全都看完了”,易行健自豪地说道。
16年后,易行健仍然怀念当时的生活。他感谢复旦在他经历经济困难、亲人重病时给予他那样自由而无用的生活,复旦给了博士生自由发展的机会,提供多种选择,而且整体的氛围较为宽松,这让易行健的焦虑与压力缓解许多。“虽然大家都是开玩笑说这是复旦的民间校训,但实际上真有这种风格。”易行健坦然道。
这种自由而无用的精神,也融入了他的灵魂。在易行健看来,自由是物质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自由地探索无限的思维空间;而无用则是学习那些对人有深远影响但短时期看起“无用”的知识。易行健觉得,人在江湖谁能不挨刀,人在江湖不能总挨刀。但是这种自由无用的精神能让人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离出来,思考更长远的东西,终生受益。
在复旦:与著名学者为伴
除了有自由的生活风气,在复旦还有大师相伴。除了易行健的恩师谢教授,张军教授、袁志刚教授和华民教授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牛顿说,如果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易行健忆及当年,在电话另一端感慨复旦经院几代著名经济学家带给自己的帮助。在他的故事里,张老师传授治学思维,袁老师开拓宏观经济视野,而华老师则教会了他严谨的思辨能力。
易行健当时参加了张军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研讨班,“他当时给我们发了很多的英文论文,并作为资料供我们复印,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当时感觉不明显,但是过了一年,在我自己写论文的时候就很明显了”。易行健说道,张军老师当时让他们阅读的这些国际顶级期刊文章,提供了先进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为易行健随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思路。
而且,张军老师的最让易行健敬佩的在于他选题与治学的思路。在研讨课上,张军老师曾向他强调,作为经济学者,在做研究时不要选择Problem,因为Problem是用来解决的,这类偏实践议题应交予企业家和政治家来解决;应该选的是Question,因为它是用来回答的。经济学家应该去回答疑问,通过回答抽象的疑问,提供给实践者解决Problem的思路。“这一点,我也经常和我的学生讲,”易行健说。或许在他看来,张军教授的阐述,正解决了他心中对于治学Question的选择。
此外,易行健对袁志刚老师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讨论班也记忆犹新。当时的袁老师刚从国外访学归来,在复旦的课程主要探讨麻省理工学院的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教授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易行健对这门课的海量内容印象深刻,“当时这门课我跟了一年,课上推导的公式模型是一黑板一黑板的。袁老师也组织他的学生来推导,自己做点评”。这门课给了当时有心做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易行健很大启发,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虽然易行健此后还是选择了别的研究方向,但是这门课的内容,为老师给学生教初级到高级宏观打下了基础。
而华民老师开设的高级国际经济学研讨班则是易行健的必修课。这门课融合了国际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内容,每节课让学生讲述一些顶尖的英文期刊论文,讨论完后华老师再给点评。“从他的点评中,我感受到了逻辑的重要性”,易行健说道。和袁老师的课一样,华老师的课也强调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背景相融合,学以致用。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在复旦的日子里,易行健有幸聆听复旦几代著名经济学家的教诲,旁听了不同老师的课程,积极参与众多的学术讲座,其中还包括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他们的思想进行碰撞,学习他们的精神,再将所学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一代代,生生不息。
深耕理论,严谨治学
“易老师在学术方面非常严谨负责,不允许我们在学术研究上有丝毫怠慢,否则他也会不保留地提出批评,这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也是我工作和学习的榜样。”易行健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
回看易行健的叙述,这种严谨有迹可循:寄给复旦尹老师的请教咨询信是线索之一;另一个则是易行健所做的毕业论文,在易行健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故事的开头充满了巧合。易行健在浦东一家证券公司研究所做兼职时察觉到了中国货币结构的变化较大,结构变化和股票市场似乎有相关性,于是便开始了研究,并最终定下题目为《经济转型与开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函数: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为了做这篇博士论文,易行健在复旦的中外数据库翻阅资料,惊喜地发现,复旦经济学院老院长陈观烈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带着手下三个学生对该领域做过探索。于是赶紧去复旦的文科图书馆去翻阅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他还发现中科院的邓述慧教授在带着几位博士生做货币需求函数,于是托数学专业的朋友将他们的论文复印过来。
刚解决了部分困境,易行健又面临数据缺失的难题,在80、90年代,很多数据都是缺失的,需要自己在资料堆里翻找,再进行倒推。“我当时去了复旦的几个图书馆,后来又来到上海图书馆,在那种黑乎乎的资料库里面,带着一支笔把那些数据一个个记到本子上,再回来处理”,易行健说道。当时的他以每季度一章的速度写作,共写作了五章。回忆过往,易行健也表达了他的遗憾,一是文章缺少了些理论建模,二是觉得文章使用了较多简约方程,而非结构方程,后者更凸显微观基础。
此外,易行健的海外交流经历更加深了他治学的严谨性。2005年9月,易行健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去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交流资助。易行健对其课程设置深有感触,学校对经济学基础课程的设置让人惊叹,“这里的宏观、微观和计量这三门课,博士生开了整整一年,一门课一个星期有九节”,易行健感叹道。而2013年去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访学,则让易行健对创新的理解又加深了许多。作为西方经济学科的中心,美国汇集了最为顶尖的经济学研究者,“我当时参加了美国的经济学年会,那个会是近万人参加,2000多场报告。”在美国交流时期,易行健笑称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听2~3个报告,“有经济系和商学院的联合报告,也有经济系自己的报告,还有社会学系的报告”,易行健饶有兴趣地回忆道。
“这些报告,天马行空的很多”,易行健说道,“但是听作者讲了以后,发现这个东西是很有逻辑的,能用理论、数据和各类因果识别方法证明出来。”易行健在采访中也感叹中国目前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虽然和欧洲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但还是与美国差别挺大,究其原因,还是研究的视野不同。在易行健看来,美国的研究更加宽泛,有做纯应用的,也有不少人做纯理论,当然更多的是两种混合的,还有人去做跨学科的研究。他指出,很多研究短时间看来是无用的,但是长时间却能显示出很大的创新,能起到一个学科对人类思想的推动,而中国却更多地执着于实用性层面上。此外,易行健还谈到了国外学者的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一位在MIT的教授,其论文竟花费五六年的时间去做实验和调查,收集数据,而且做完之后还去积极讲学,通过同行审议,吸取意见来提升文章质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易行健将他学到的经验运用到了他自己的学院管理和学术质量提升当中。广外金融学院的一位本科生告诉记者,易行健在学术氛围、学术态度和学术道德方面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博览群书。而且有组织地开展了许多科研工作,邀请学界知名学者来校作学术讲演,举办多场讲座和学术论坛,平时也会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和文献,定期考察学生对学术著作的理解。
易行健的严谨获得了回报。他在2004年博士毕业后一段时间内继续推进博士论文选题的研究,经过4年多时间就被评为教授。当时在广外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担任科研副院长,中间有几年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比较感兴趣,近年来又将重点转向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与家庭金融行为。易行健表示,2001年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主攻了4个问题: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是否稳定、开放经济对中国内生增长的影响、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为什么这么低、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财富优化问题。他基于四个问题的研究出版了3本专著且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完成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和两个国家自科面上项目和其他一系列项目。易行健在高标准的写作要求下,笔耕不辍,知网总发文量已达120。

“我真的是尽自己所能把这个东西往前推一点点,这个点多大,我也不确定,只能是尽自己所能推动我们对金融经济运行规律的了解,想要更多一点点。”易行健坦然道。国家也对于易行健科研成果表示了认可,他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还获得其他学术荣誉等。

易行健教授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社会责任感贯穿了易行健的人生。
易行健成长的80年代和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从乱世到安定,社会的创伤在治愈,从中央到民间,人们在探索振兴中华的正确途径。易行健的爷爷就曾向他传达过这种社会责任感。“我爷爷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易行健讲道,言语中透露着自豪。
随着易行健的成长,他从湖南的村子走到了上海,见到了更多怀着理想主义的人们,比如曾给他上过课的张军老师,他们身上的家国情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易行健。“我们当时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么落后,怎么样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想法,以及自己的发展怎么样能和国家的发展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基于此,我们读书是非常认真的。”易行健说,这一点也在他的研究历程中显现出来。从关注中国货币结构的博士论文,到后来深入探究作出的《经济开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函数:中国的经验》和后续三个主要问题的研究,易行健践行着自己的信条。
在采访过程中,易行健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在读博士的后期就在湘潭大学商学院金融系担任系副主任,2005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后担任经济系主任,2006年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访学回来后不久就担任学院的科研副院长。2014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访学回来后就一直担任广外金融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同时,他还结合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的需要,牵头成功申报了一个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金融开放与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以及一个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
在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余,易行健在领导学术机构、培育学术团队和思考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以及为区域与国家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与参与咨政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这些工作虽然比较繁重,但是易行健表示,他在其中感受到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律动,体会到人才培养的点滴收获,与学科和团队一同成长。易行健向记者回顾着10多年的各类社会服务工作,他的话语中充满着一种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
在采访结尾,易行健和记者谈到了对人生的看法。他感叹地说,今年是他博士毕业的第16年,时间不长也不短,在过往的日子,也做出了些许成绩。对于自己选择教师这一职业道路,易行健坚定地表示绝不后悔。从读博到做教师,他觉得过程虽然艰辛,但是也很快乐。
而对于未来,易行健也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精神:“希望能把我的学术再做进一步的拓展,解释未来几十年中国走向发达经济体和实现伟大复兴过程当中的经济金融结构问题,在著书立说的同时能够做好‘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职工作。”此外,易行健还谈到了自己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职责。他希望把这个学科再向前推进一步,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作出一个学者应有的贡献。
采访至此,已近结束。记者问了易行健一个“私人”的问题,鉴于易行健如此热爱武侠小说,那么他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呢?
“那就是金庸笔下的郭靖吧!他的出身并非我们认为层级很高的人,但是他的一生秉承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易行健说道。


易行健教授外出旅行
来源:“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