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谢希德校长接触不多。
但是她对我提携和帮助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
作者:周午纵 1978级化学系校友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
1982年,我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当年复旦从5个理科系各选择了3位毕业生,以留校助教的身份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我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十余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英语培训,就着手申请美国的大学。
那个年代我们能获得的信息和资料都非常少,对于西方国家的情况,除了略知那里科技发达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去向某个大学索要大学信息和申请表,常常需要等待几个星期才会收到答复。

▲恒隆物理楼
一天,我经过物理大楼,看到谢校长步履蹒跚地从楼里走出来,便上前想询问她从哪里可以获得外国大学的资料。
谢先生是物理系教授,我没有听过她的课。她并不认识我。而我认识她仅仅是因为她刚刚从苏步青教授手中接任复旦校长,在某个大会作报告,给我留下一个慈祥老太太的印象。看到我走近,她停下脚步,听我自我介绍是化学系刚毕业的学生,准备出国留学,却苦于找不到国外大学资料。她低声细语地说:“我正要去行政楼参加校长会议。不过还有8分钟。到我办公室找找看吧。”于是就领我返回物理楼二楼她的办公室。她上楼梯时,提脚似乎有些艰难吃力,我当时是第一次发现她有腿疾,又被她出乎意料的果断决定惊到了,竟没有意识到应该上前扶一把。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叠材料,从其中选出几份美国大学的申请表说:“先看看这些吧,现在我要赶过去开会了。”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完全没有对我的冒昧表示责怪。我后来填写了其中一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申请,并获得了录取通知书。
正在我准备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谢校长有一天说要见我。还是在她的办公室,还是那样低声细语,她说:“中美科技文化交流的人数目前大幅度减少。今年政府给我们复旦大学到美国访问和留学的名额仅有6名。我们有一大批年纪较大的老师排着队等待去美国呢。考虑到你还年轻,这一次是不是可以让一下?”
我当时心里老大不高兴呢。但是,看到谢校长如此平易近人地对待一个年轻学子,再大的委屈也说不出口,只能默默地放弃了去俄亥俄留学的计划。后来的一年多时间,我在化学系催化楼做研究助理,借调到北京国家科委基础研究局工作,出国的热情慢慢地减退了许多。
再一次去见谢校长已经是1983年底了。她站着,一边翻动着一堆文件,一边对我说:“你应该申请出国去读博士学位。美国去不了,可以去欧洲嘛。”我说:“我只读过英文,到欧洲语言不通啊。”她心平气和地说:“英国人也是讲英语的呀。何况,你的英语也没有学好。”
她怎么会知道的?
我突然为自己的无知和托福考试成绩不佳感到无地自容,明显觉得脸上有点发烧。随后,她拿出一份剑桥大学的申请表给我,说:“我觉得你应该申请去英国剑桥读书。我给你写推荐信。”我当时不知道剑桥大学是世界名校,即使后来听说是世界名校,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我只是顺从谢校长的建议,填写了申请表。然后,谢校长告诉我她的推荐信已经寄走了。她和当时许多老师不同,不让我看她写的推荐信。
有一天,我带着迷茫去看望上海工业大学一位老教授。他听说我在申请剑桥,连连说,不妥不妥。说中国人申请进剑桥大学念书是十分困难的。即使进入剑桥大学也都是进修一下,大多数人是拿不到学位的。接着说出一串名字,徐志摩,华罗庚等等。
第二天,我去找谢校长,讲起那位老教授的意见。我说是不是应该同时申请另外一个比较普通的学校做备份。她的表情似乎严肃了些,语气坚定地说:“你不要再申请任何学校,就去剑桥。我已经写了推荐信,他们凭啥不录取你?没有理由啊。”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偶遇,她拿出一封剑桥大学物理化学系主任John M. Thomas给她的回信,让我读完后还给她。大部分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意思是十分感谢你将贵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介绍给我,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个学生,手续在办理中云云。我想谢校长是为了打消我的疑虑才让我看Thomas教授的信。
1984年出国后的三年,我在Thomas教授和David Jefferson博士的指导下做固体微结构研究,期间没有和谢校长联系。
有一次喝茶时闲聊,我问Jefferson博士,中英教育体制不同,当年是凭什么决定录取我的。他说:“主要的依据就是你们校长的推荐信。为此我还专门去咨询了我所在的冈维尔与凱斯學院李约瑟老院长。李约瑟说谢希德的信绝对可信,不容置疑。”原来当年谢先生从美国麻省理工获得博士,回国前转道英国,和获得剑桥博士并留校任教的生物化学家曹天钦结婚。在剑桥住过一段时间,和李约瑟是老熟人。

▲
谢希德、曹天钦夫妇在英国剑桥
图片来源:《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1987年我写完博士论文后获得剑桥皇后学院Research Fellow的职位。写信给谢校长汇报我的工作情况。她很快给我回了信,告诉我剑桥学院中Research Fellow的中文翻译,鼓励我继续努力工作。
后来,我参与了剑桥大学超导研究中心的工作。期间与中心主任梁维耀教授一起编辑了一本由不同国家华人学者撰写的《高温超导基础研究》,1999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出版前,我不知道谢校长正病重住院,竟写信恳求她为这本专著写一个序。她回信推辞说,她并不是超导方面的专家,作序恐怕不合适。我又一次写信去说,再三考虑后依然觉得她作为著名固体物理学家和复旦老校长,如能为本书作序会令我们感到无比的荣幸。不久,我们收到了她数页的手稿,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位老物理学家和学界领导人对于后辈科学家的热情支持和谆谆教诲。也对高温超导的发展和华人科学家在该领域的突出贡献提出她本人的见解。后来得知,谢校长是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在病床上忍着病痛为我们写了那篇序。令我终生感到内疚。
我在谢校长面前表现得那么冒昧鲁莽,无礼无知。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都觉得惭愧,不过很快总会找到为自己开脱的理由:那时太年轻,有过错是可以原谅的。事实上,谢先生对于我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改正我年轻时的缺点,而是当我自己做了大学教授,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会常常想起她对于我一个化学系学生的宽容,厚爱和提携。我会常常问自己,我也能做到吗?很多年过去了,我才意识到谢校长给予我的短暂训导和言传身教,竟然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永远深深地怀念谢校长。
2021年2月25日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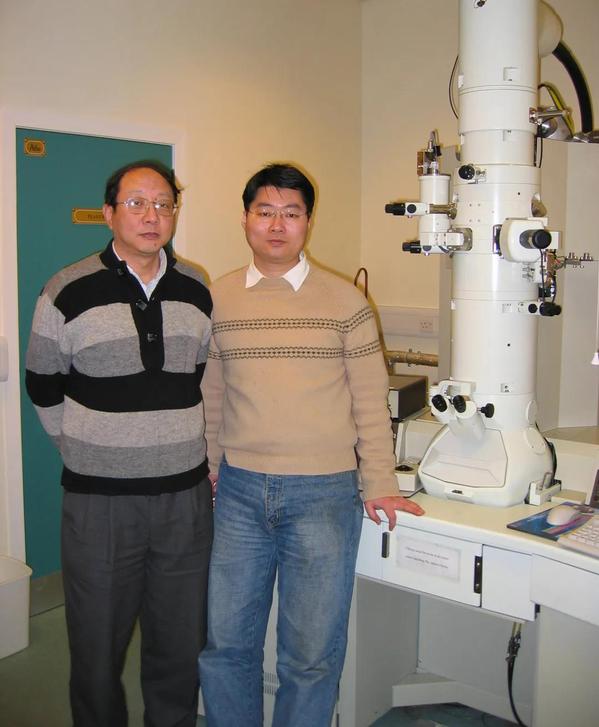
2003年周午纵校友(左)和复旦大学访问学者谢颂海(右)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电子显微镜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