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树阴浓,蝉鸣盛夏。又一批复旦人带上行囊踏上追梦的列车,驶向世界各地,贡献复旦力量。
毕业了,你会去遥远的地方,看遍世界,阅尽天下风光。也许多年后,你走累了,回忆在校园的种种过往,你会发现记忆里只有怀念、感激和美丽的时光。
当你再度回到母校,你会像当年一样,舞动翅膀,飞越高山和海洋,回到心之所向——复旦。
六月的尾巴,毕业季也渐渐落下帷幕,谨以此篇“我的复旦”,献给全体毕业生以及世界各地的复旦人。
愿每一个奋斗的青春发光发热,星光璀璨!
申剑敏 1995级国际政治系
2019年5月26日,离家不远的正大体育馆在风雨中迎接校友。我在北阳台进进出出,洗拖把晾衣服,不时凝神远望,想像着人声鼎沸和盛华灼灼。
1995年我入校,仿佛经过高考一役到达顶峰,多年后才知这不过是漫长人生的某个节点。相辉堂因我们的意气风发和人生正得意,又因其承载着厚重历史,在新生眼中变成古老雅致的校园主标识。当时它体量甚小,容不下一届新生,以至于大家必须分批入场开会。相辉堂在以后的生活中承担如下角色:携亲友打卡,校园街拍,老乡聚会,以及体锻盖章的终点。多少次清晨从东区挣扎而起,过国定路经校园主干道,一路踉跄至相辉堂前,又盖好一个章!往回走时,见舍中最有大姐风范的海燕,骑车带着最瘦弱的小鱼儿,一路飞驰而来,她俩把车停好,再跑去终点盖章。宿舍姐妹关系极佳,于是其他人屡屡吃醋,争夺有车带跑的特殊待遇。相辉堂的个人记忆来自不成功的两次自编话剧演出,算是了却文学青年未竟的梦。集体记忆当属95年的一二九歌会。法学院当时是大院,集法律、国政与社会学系之力,召集了百余新生参加歌会。学院请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校友夏旸老师兼职做指挥。夏老师温文尔雅,下班之后匆匆从市中心赶到文科楼,带着音乐素养高低不同的一众人等投入排练。从秋入冬,无数次在文科楼的楼道里,响起轻吟和低唱,那是参加排练的我们深夜而归。然而法学院最终惜败!我们眼眶湿润了,在比赛结束后自发整队上台,夏老师一声叹息,把外套脱下又用力掷于地上,两手一扬,再度指挥起《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悲壮与激愤的乐章响起,法学院唯一的一次集体出演黯然落幕。

▶ 1995级国际政治系新生入学留念
1995年的校园东北角,是一店(旦苑)、一池(游泳池)、一场(射击场)和一馆(体育馆)。旦苑仅一层,菜略贵且多油,有朋自远方来时,去此处点个小锅菜颇能撑得了台面。旦苑旁的小电话亭永远人满为患,乡音弥漫。我和舍友去游泳池游过几次,遗憾的是没有自学成才。游泳池的后面是一个小型射击场,96年暑期军训,不少同学在这儿打响了人生的第一枪。体育馆是当时闻名上海东北片的一处胜景,因为附近高校的学生喜欢周末到体育馆跳交谊舞。女生通常一排排坐在观众席上,不知哪个高校的男生陆续进场,仿佛逡巡一般在馆中游荡,目光交错,两两对望之后,一个短暂或长久的校园故事便在舞曲中开始了。沿东北角往校园深处走过,在进入“南京路”之前经过零号楼,这栋不起眼的L字型小楼,彼时因设置院系信箱成为信息中枢,一楼入口处还有一家裁缝店、一个复印店和卖日用品的小商店,1995年入学第一周,我在那儿买了人生中第一盒上档次的面霜,24元的夏士莲,它散发着似有似无的淡淡清香,让我深感大学的美好。

▶ 1996年暑期军训作者与舍友的合影
从零号楼拐个弯,便到了大学后面两年居住的五号楼,即今天的校医院。97年搬到五号楼前和几个同学踩点,分到的舍前尚堆放着小山般的废弃棉被和衣物,它们的主人却坦然撤离了。一至三楼是经济学院女生,四至五楼分给法学院,被戏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东宫”搬到校园里,男生终于突破东区门卫的藩篱,在宿舍楼门前拿着热水瓶和饭盆,三三两两等着女友去自习。我的宿舍543堪称最佳观景处,远可见文科楼与李达三楼,近可俯瞰篮球场,往里一看则楼道动态一览无余。隔壁最用功的女生是法律系学霸,总在深夜走廊的灯下背着法条或英文,让看完小说后上厕所顺路经过的我颇感羞愧。在她们的激励下,我也曾深夜坐在转角楼梯,前面摆着高凳,以勤奋的姿态完成了数篇课程论文。

▶ 1995年东区宿舍内景

▶ 1995年作者与舍友的合影
法学院第一年的课程不分专业,印象中在3108或是3106,三个系的学生一起修完了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原理类课程。上社会学原理的是刘豪兴老先生,上课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我却还能听懂,故而也颇为得意地给舍友作了翻译。二教侧面的一间大教室中,上社会心理学课程的孙时进老师,某次课上给大家做了集体催眠,在他的循循善诱中,有多少同学真的入睡?三教地下有间听音室,颇受外地学生青睐,凭借哑巴英语挺过高考的我,既听不懂英语老师授课,更不谈如何能应对听力考试。无它良策,只好经常潜入地下,领得一盒磁带和一副破旧的耳机,在颇感阴森的听音室苦练“英国老鼠”。

1995年收到的复旦通知书上,赫然印着“邯郸路220号”。当时邯郸路周边既无中环通过,也无五角场商圈,校门前有条人行地道,据说是80年代为方便师生出行而修建的便捷设施。一次到文图看书,地道中遇见匆匆而行的蒋昌建老师,我与舍友几乎是欢欣雀跃,紧紧尾随几步,又怕他回头发现,只恨手中没带着《狮城舌战》,让最佳辩手签名赠言。蒋老师可知?经狮城一战和他仰首喟叹的康德语录,让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学子在高考志愿一栏,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复旦国政。通过地道,便是在邯郸路另一端的复旦教学和生活区,除文图、文科楼与五教六教外,还有十多个生活小区。这是如今郊区大学城无法享受的“福利”——一个融合于市民生活中的大学,这让复旦总带些日常烟火气,温暖又真实,长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藉此便利,我们在邯郸路另一头活动时,时常看到穿着随意,拿着菜篮子或带着孩子的老师,也到不少老师家中做过客,在辅导员陈超群老师(我们称为“超哥”)简陋狭小的教员宿舍中,听他激情讲述自己研究的生存哲学。彼时的师生之间,没有项目课题的捆绑,没有利益资源的交换,年长的如长辈,上课循循言及人生;年轻的亦师亦友,系中一位刚留校不久的年轻老师,一次上课迟迟不来,我们在教室中苦等半节课后,老师冲进教室,喜气洋洋地宣告,“女儿上午出生了!”7位上这门课的政治学专业同学,课间凑些钱,跑到超市买了包纸尿布送给老师,这是真诚地分享喜悦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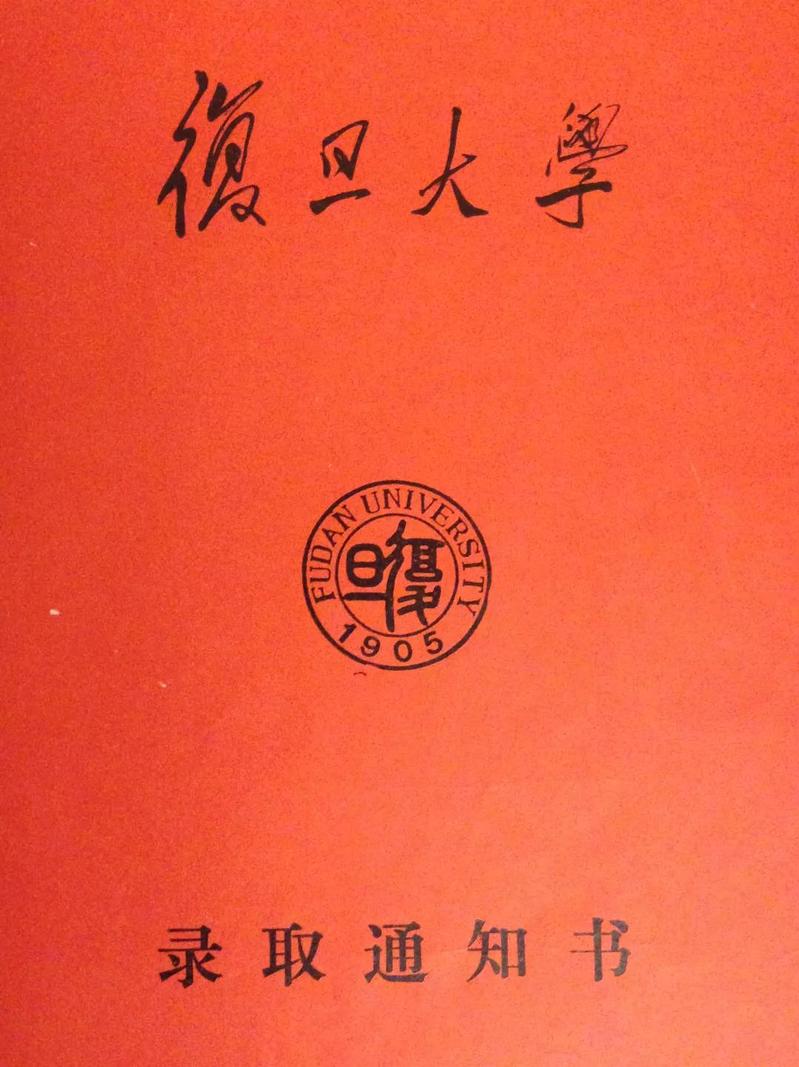

1997到1998年间,校园中有些不大不小的改变。叶耀珍楼大约在1998年修建完工,一楼教育超市开张,二楼建了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厅,大家沙龙也正式搬到叶耀珍楼,除继续讨论诗歌与哲学之外,开始出售咖啡和茶点。在沙龙里,印象中我曾喝过几次8元一杯的咖啡,也欣赏了复旦诗社的吟诵……80年代到90年代间,复旦诗社与燕园剧社同为全国高校文化活动的两大主阵地。这一时期,我们543集体生活也有起色,舍友们凑钱买了台386的二手电脑,高调进入电子化的写作阶段。美中不足的是,电脑键盘有些老化,输入速度很慢,在论文写作高峰时段,只有合理安排档期才能兼顾彼此。大学后两年的生活随意散漫,同学们因兼职或家教,袋中多了些除口粮之外的余钱,故不时呼朋引伴。几家散布于复旦周边的大排档中,年年红、德利、川妹子等成了聚会首选,每人5元,大抵凑个40或50元,便可在排档吃一次小炒以改善生活。

▶ 1996年寝室联谊活动

▶ 1999年毕业合影留念
1999-2019,毕业20年,致 复旦 与 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