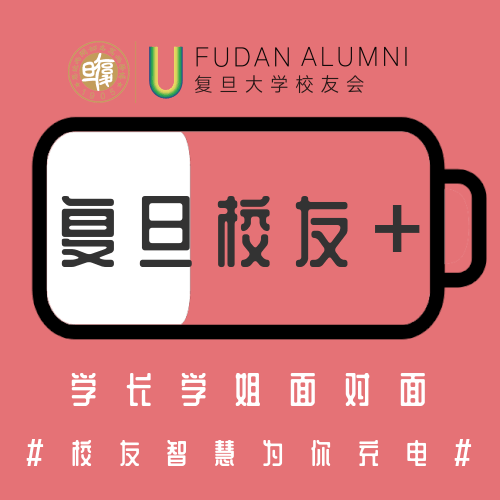BY 19级新闻学院王正珺
冀耕学长2010年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接着去了云南大学读硕士。本科五年加上研究生三年,冀学长一共学了三个专业——基础医学、历史学、人口学,不仅各不相同、跨度也挺大。原来学长高考时报的专业是化学,但被调剂到了基础医学。从大一伊始,冀学长就加入了剧社、开始演话剧,话剧的魅力令他这个理科生对文科产生兴趣,越来越倾向于往文科方面发展。对医学的兴趣寥寥,让冀学长在大三时选择转到了历史系。
关于那次转专业,冀学长当时是有纠结的。“我现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工作,主管研究生教育这块儿,我发现 ‘读书惯性’现象在学生们中很常见,很多人继续往下读都是一种潜意识的惯性。本科时我也有这种想法,我想既然读了医学、要不要坚持下来,比较纠结要不要走出来。”为什么会选择历史学呢?冀学长说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我父母都是大学历史老师,他们经常吃饭的时候讨论历史问题、吃着吃着开始争论,饭也不吃了就去翻书。” 冀学长笑着说,“我就是在历史的熏陶下长大的,所以转去了历史系”。
到了研究生,因为一分之差,冀学长又被调剂了,这次被调剂到了人口学专业。“虽然一开始对人口学不太了解,但是学起来挺有意思的,涉及到很多社会性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性别和权利等等。人口学专业也让我学了很多统计方法,和之前历史学的史料研究很不一样。”
本科毕业时冀学长曾经在企业找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但最后还是“稳住了”,选择了先考研。读完研究生后,冀学长选择到高校工作。谈及为什么会选择到高校做行政人员,学长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由于父母是大学老师,我从小就是在高校里长大的,所以研究生毕业后,挺单纯地就想在高校里工作。而且有寒暑假,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选择回到广州,是因为想多陪伴父母。
在暨南大学,冀学长先是做了一年的合同工,第二年考到了编制,成为聘用制员工。合同制和聘用制相比,后者的福利待遇更好,但是竞争也更加激烈。学长记得那一年有1000多人报考,最终录取的名额不多。虽然合同制的工资不高,但是学长建议可以先做合同工了解工作性质、熟悉工作内容,再考编制,也不失为一种进入体制内的方法。
关于工作内容,学长觉得做行政和本来的专业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和公文、表格、数据打交道。工作之前,他以为行政的工作很简单,随便抓一个人就能做,但是工作后发现不是这样,还是很考验一个人做事不拖沓、处理好同事关系的能力。有的时候领导布置工作时一句话就讲完了,比如说“把xxx做一张表”,但是真的做起来,会发现想要做得全面、美观,还是很需要思考的。
谈及行政岗位和辅导员的差别,学长认为辅导员工作更脱离办公室,要和学生打交道、和学生谈心谈话,要做党务发展,还要抓学生就业。虽然他是坐办公室,但冀学长经常和学生们“混”在一块儿,从2017年开始,学长负责带学院里学生的暑期实践。此外他还是篮球队教练,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打球。
处在就业的岔路口,我时常感到迷茫,拿不准毕业后到底从事哪个行业,亦或是考家乡的选调生。在与冀耕学长长谈一个多小时后,我发现高校行政对我而言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聊天的过程中,学长也给了我一些建议,首先,他建议我做好心理准备,不要觉得高校就一定单纯、简单,办公室文化在高校也很常见。其次,他建议如果想进高校工作,可以选择一个熟悉的城市,或者熟悉的学校,比如可以留在复旦。最后,他也提到行政工作繁琐,有时候会很忙,他曾经忙到连饭都不能步行5分钟回家吃。
今年正值冀学长毕业10周年,趁暑假他回到了上海,和许多昔日的同学聚会,也拜访了恩师。虽然已经毕业10年了,但是他觉得同学们变化都不大,都还有以前的影子。“但遗憾的是不能进到校园,只能在外面看一看。”
是啊,7月返回上海后,我也路过了好几次复旦,但是都不能进去。我们共同盼望着,校园开放的那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