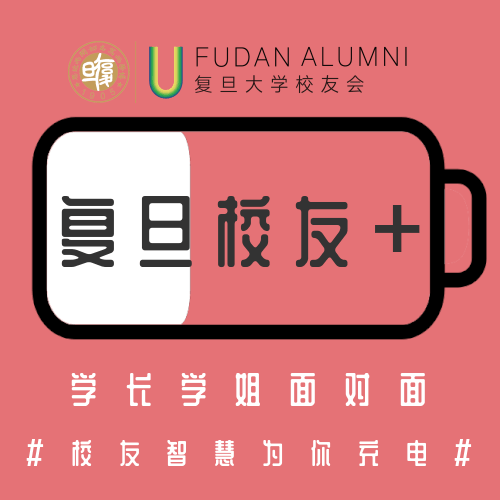BY 18级中文系娄徐均
从复旦出发
2014年,孙菱羲从复旦中文系本科毕业,保研至中山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继续深造。硕士毕业后,她选择返回家乡贵州,继续从事深爱的文学事业,并创办了自己的私塾。
回顾在复旦求学的那些日子,有太多璀璨的记忆留在她心中。例如骆玉明老师在《世说新语》课堂上,灵感文思常如行云流水般自由地流淌,偶然触及某个沉痛的点,语言又会戛然而止陷入沉思,有时甚至还会令坐在一旁的同学们因感触良多而哭到不能自制。不论是魏晋人物身上潇洒高昂的精神,还是骆老师个人丰沛的思想与生命力,无疑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孙菱羲之后学业与人生方向的选择和发展。
与此同时,浸润于复旦开放、包容、自由的风气中,亲身体验逐步开展起来的通识教育,欣慰地见证昔日的伙伴们在各个领域内发光发热,有的出国深造,有的就职于各类企业,还有的成为了业余作家等等,她仍感恩于复旦为学生铺垫的多元优势,和提供给大家的精神视野,
打造文学的课堂
孙菱羲是一位“自足”且怀揣理想的中文人。硕士毕业后,她经过清晰地思考,决定回到家乡贵州,并且拒绝了长辈期望的“稳定”工作,而选择自己开办私塾,分享自己在中文领域收获的感悟。她的课堂“有教无类”,不仅有小朋友、中学生,还有来自不同行业的成人爱好者。
她努力搭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使文学的知识与教育以真正有价值的方式展开。从文明的初创到近现代的各类文学经典,从原典阅读到专题写作,她的课程涵盖了丰富的内容,既做到了实用性的衔接,又提供了更立体、更深入地艺术文化熏陶。在启迪学生心灵的同时,也能对学校的语文教育进行拓展和补充。
中国文学在孙菱羲眼中,是一个能够带领我们超越局限进入广袤世间的窗口。“人到中年,一地鸡毛”是许多职场人的感慨,忙碌、焦虑、压抑、麻木充斥着日常的工作生活,但正因有了这些人生体验和阅历,再来接触中国文学时反而会有更深的感悟。孙菱羲介绍道,“比如读到《道德经》《传习录》《人间词话》这类经典的时候,成人学员给到反馈和共鸣其实是最多的。”文学看似“无用”,却能给予心灵美的享受,给生活带来调剂和指导,更能召唤出我们内在强烈的觉察力和生命力。
平日里话不多的她,认为“课堂上可能是我最安心、最滔滔不绝的时候,学员的反馈和课堂质量也是我最放心的。”因为教学相长,使她更懂得理解与倾听他人,更懂得以恰当的方式给予他人需求。借助“文学”这个小舟,她也认识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她坦言自己其实是那个收获最多的人。
保持热爱和学习
在开班授课的过程中,孙菱羲自然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例如刚毕业的她,外表看上去显得青涩而稚嫩,常常在初见时受到家长的质疑;在招生宣传方面,她也完全陌生,因此招生总是显得得很“佛系”;最早没有专门上课的教室,就让学员坐在家里客厅的地毯上听课,不过后来学员都反馈说,这样别具特色的“地毯沙龙”令课堂氛围更加轻松愉悦了。与此同时,家人对这样的自由职业,也充满着担忧。在这般局面下,她依然坚定自己的想法,大胆尝试,努力成长。幸运的是,但凡听完她的课之后,家长的疑虑便会打消,而渐渐产生很强的信任感。
“文学可以带给生命和心灵深厚的滋养,但遗憾的是它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个令学生痛恨的考试知识点。”谈及当下的语文教育,孙菱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所谓‘语文’是中国语言文学艺术的简称,艺术是多元的、丰富的,但语文考试却拿着一个标准和模板去套,它早已失去了艺术的模样。”她点出了当下教学的痛点,认为单一的目标导向需要朝着更多元、立体、活跃的方向发展。近年来的语文考试,对于语文综合能力的考察大幅提升,对语文素养的积累、分析与写作能力的考察也大大增加,这也算是课内教育的新改善。
为了保持学习和常新的状态,孙菱羲也即将前往中山大学继续读博深造。与此同时,还与来自牛津、剑桥等世界各大名校的伙伴合作创办“泊言馆”,致力于不同语言文化的教学和交流,开发不受地域限制的线上课程,以便她能在学业之余坚持开展自己热爱的事业。一方面,正是因为她认真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一直保持很大的备课量,从未中断读书;另一方面,她在教学过程中也常有缺乏同行交流的孤独感,以及为了能对逐渐成型的课程体系有新的补充,因此她抱持着提升的心愿,选择在中文领域继续前行。
不论是当初保研、工作的选择,还是回归校园继续深造的决定,孙学姐都非常明确自己的心意。中文系出身的她,始终践行着有力的自我觉察。最后,学姐也为学弟学妹们送上祝福,“骆玉明老师曾说,人生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活得精彩。希望复旦的学子们能够全然地投入和体验生命,因为心灵丰富才会有文学。”